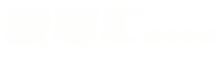广发宏观:新一轮技术变革的宏观分析框架
报告摘要:
历史上经历过五轮影响较大的技术革命。第一轮是1771 年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化生产的广泛应用;第二轮是1829 年开始的蒸汽动力与铁路时代;第三轮是1875 年开始的钢铁、电力及重工业发展;第四轮是1908 年开始的石油的大规模应用和汽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大规模普及;第五轮是1971 年开启的信息与远程通信时代。目前有可能已处于第六轮开启前后,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的发展将成为引领性的产业趋势。
1佩蕾丝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以及2弗里曼和卢桑在《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中曾对历轮技术革命中的标志性技术、关键要素、主导产业、生产组织方式等做了梳理。在2025 年1 月的《跨越多周期叠加:中期宏观环境展望》中,我们曾对其做过初步介绍。
技术革命周期和宏观经济分析上经常说的“康波周期”具有相互匹配性。康德拉季耶夫分析了英、法、美、德等国100 多年中批发价格、利率、工资、煤炭与生铁的生产消费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大量统计数据,发现经济中存在着48 年到60 年、平均为50 年左右的周期性波动。1939 年,熊彼特将其命名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国内研究一般简称为康波周期。
根据佩蕾丝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是从新的关键要素到新的经济范式,其中涉及产生关键要素的动力部门(motive branches)、大量应用关键要素的支柱部门(carrier branches),以及进一步催生的引致部门(induced branches)。每一轮技术革命的共性包括:(1)驱动部门产生新的关键要素,并跨行业被大量部门所需要,只有少数行业需要的不算关键要素,历史上比如铁、煤、钢、石油、芯片等都是关键要素;(2)关键要素价格的迅速下降是量变催生质变的标志,它会进一步带动通用技术的扩散,以及依赖关键要素的支柱部门快速增长;(3)技术革命最终催生新的经济范式,但这一过程的形成需要时间。
1985 年3佩蕾丝提出技术-经济范式,用来解释技术革命和经济长波的关系,2002 年在著作《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中,进一步完善为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技术-经济范式理论认为,历史上出现过五次技术革命,产生了相应的五轮技术-经济范式。技术革命得以扩散的载体就是技术-经济范式,它有效地利用了每一次技术革命所带来 的创新潜力,是经济主体运用新关键要素和新技术的最佳实践 模式。
第一次技术革命的关键要素是铁,随着冶炼工艺的突破,特别是搅拌法(puddling process)在铁矿石冶炼及生铁转化为熟铁过程中的应用,熟铁的供应量大幅增长,从1788 年到1815 年增长了500%,与此同时,铁的价格大幅下降,从1801 年的每吨22 英镑降至1815 年的每吨13 英镑。此外,拿破仑战争期间军需品需求的急剧膨胀,以及工业革命中民用需求的快速增长,推动了熟铁在各个行业的普及应用。在这一时期,工厂制逐步取代传统的手工作坊,支柱行业主要为棉纺织业和冶铁业。经济结构以小企业竞争为主,合伙制企业兴起,生产方式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流。
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关键要素为铁和煤,尽管煤炭本身并未经历技术创新带来的价格剧烈下降,但蒸汽机和铁路的出现极大降低了煤炭的运输成本,从而使其得以在多个行业得到广泛应用。铁路成为这一时期的核心支柱产业,钢铁和机械制造业迅速崛起,推动了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化。与第一次技术革命不同的是,大企业开始出现,股份有限公司和风险投资模式逐渐普及,为资本积累和产业扩张提供了制度保障。
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关键要素是电力和钢,19 世纪50 年代至80 年代,贝西默工艺的发明与推广大幅降低了钢材的生产成本,使其在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包括电力工厂、铁塔、发电机等。在这一阶段,电气设备、化工和重型机械成为主导产业。产业组织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垂直整合的巨型企业兴起,官僚制管理模式普及,同时泰勒科学管理(Taylorism)成为提升生产效率的重要手段,企业内部的研发部门逐步实现专业化,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
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关键要素是石油和天然气,19 世纪60 年代,全球石油产量仍以百万桶计,而到了1939 年,石油产量已跃升至十亿桶级别,充分满足了“普遍可得”的标准。在1910 年至1939 年期间,石油产业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其增速远超同期全球工业生产的整体增速。与此同时,石油价格也从19 世纪60 年代的较低水平逐步上升。全球石油供应链体系随之迅速扩张,油罐车、集装箱、货车以及炼油厂的数量均实现了成比例增长,为石油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汽车工业和大规模生产模式成为经济的核心,石油化工产业迅速发展,高速公路网络逐步完善。福特主义(Fordism)所倡导的标准化生产模式主导了制造业的发展,跨国公司加速扩张,消费市场逐步大众化,形成了全球化生产与消费体系的雏形。
第五次技术革命的关键要素是芯片,从20 世纪50 年代到90 年代,芯片的集成度经历了从小规模集成到超大规模集成的跃升,元件数量呈指数级增长。然而,与前四次技术革命不同的是,芯片产业的兴起并非依赖单纯的市场驱动,而是由美国政府主导,通过扩大设计和生产规模来降低成本、提高性能,从而推动芯片技术的突破性发展。随着芯片技术的成熟,信息技术、半导体和通信产业迅速崛起,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在这一阶段,网络化企业(如微软、英特尔)逐步取代传统制造企业,灵活生产模式取代了过去的大规模批量生产方式,知识资本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信息密集型行业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
每一轮技术革命可进一步划分为导入期(Installation Period)和展开期(Deployment Period)。导入期又进一步包括爆发阶段与狂热阶段。在爆发阶段,新技术初步出现并引发投资热潮,金融资本主导,技术创新与投机泡沫并存;至狂热阶段,技术应用快速扩散,但市场泡沫逐步退潮。展开期进一步包括协同阶段与成熟阶段。
协同阶段的特点是技术逐渐成熟,开始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社会制度(如政策、法规)开始适应新技术,形成稳定的“技术-经济范式”;至成熟阶段,技术已经全面普及,并开始相对稳定地助力经济增长。
根据“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当颠覆性技术集群突破既有生产体系,将触发长达半世纪的结构性变革周期,这种变革通常呈现双相演进特征:前三十年的技术导入期与后三十年的范式展开期,两阶段间往往以系统性经济危机为分水岭。这种周期性震荡不仅重塑产业格局,更推动着社会制度的深层变革。
在技术革命的“导入期”,即技术扩散的初始阶段,革命性技术犹如楔入旧经济体的异质元素,通过创造性破坏 重构生产要素配置。此阶段以基础设施重构、商业模式试错、金 融资本聚集为特征,通常引发生产要素价格剧烈波动与社会财富再分配。导入期的本质是新经济范式确立主导地位的过程,此时技术红利开始全面释放。当技术渗透率达到临界点时,系统将经历"范式转换阵痛",表现为大规模经济衰退与制度框架重构,这标志着技术周期进入“展开期”,展开期的前半段是这一轮技术革命的黄金时代,增长趋于稳定与和谐,而后半段则是技术范式逐渐成熟的时期,市场逐步饱和,经济增长模式接近极限,并酝酿着下一轮技术革命的到来。
按照佩蕾丝的划分,第一轮技术周期是以英国为首的工业革命,导入期历经了22 年(1771-1793 年),展开期则是31 年(1798-1829 年)。第二轮技术周期是以英国为首的蒸汽和铁路时代,导入期历经了19 年(1829-1848年),展开期则是23 年(1850-1873 年)。第三轮技术周期是以美、德为首的钢铁、电力和重工业时代,导入期是18 年(1875-1893),展开期是23 年(1895-1918)。第四轮技术周期是以美国为首的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时代,导入期是21 年(1908-1929),展开期是31 年(1943-1974)年。第五轮技术周期是以美国为首的信息和远程通讯时代,导入期是30 年(1971-2001 年)。由前五轮技术周期的展开期平均时间26 年外推,当下可能位于第五轮技术周期和第六轮技术周期的叠加共振期,信息技术革命的展开期(2001-2030)与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的导入期(2015-)形成历史性交汇。
关于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典的理论主要是卢卡斯和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内生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视为内生变量,通过人力资本积累、研发投入、知识溢出等因素推动,技术是一种可积累的公共品,会不断地作用于经济。创造性破坏理论则认为技术创新的本质是结构性变革,是新技术对旧技术的替代,以及它带来的市场垄断权的更迭和产业结构的重组。简单来看二者区别,内生增长理论之下,技术革命是线性的、连续的;创造性破坏理论之下,技术革命是非连续的、跳跃性的。从“创造性破坏”理论的角度,似乎更能理解产业政策的意义,政策可以在新旧技术替代的关键时段对创新形成助推力量。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以4Romer(1986)和5Lucas(1988)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Theory),发展推动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该理论强调技术进步是内生的,资本积累与创新共同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而熊彼特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该理论认为一旦创新成功,创新企业便能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将原有企业淘汰,并获得垄断利润。在此理论基础上,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了垂直创新(vertical innovation)和水平创新(horizontal innovation)框架。垂直创新指通过研发不断提升产品质量,高质量产品逐步取代低质量产品,从而推动技术进步。相比之下,水平创新则通过研发拓展生产投入品的种类,进而促进专业化分工,以推动技术进步。
新近的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扩散假说也是一个重要框架。它认为通用技术可以通过产业链重构与网络效应推动长期增长。这一假说对技术扩散的理解和佩蕾丝的框架本质上是一致的。它认为通用技术的扩散并非一蹴而就,其对经济的影响可分为两阶段:播种期(Sowing Time),即技术研发与基础设施投入阶段,社会资源大量消耗但回报有限,这一时期产出和生产率增长缓慢甚至下降;收获期(Reaping Time),即技术规模化应用阶段,生产力跃升与结构性变革带来产出和生产率指数级增长。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例,播种期(1760-1800)对应的是瓦特蒸汽机发明后数十年内,技术仅用于煤矿排水,社会投资集中于铁路与冶金业;而在收获期(1800-1840),蒸汽动力规模化应用于纺织、运输业。电力革命(1870-1950)时期,播种期(1870-1920)时发电机与电网建设耗资巨大,工厂需重构生产线以适应电气化;而在收获期(1920-1950),流水线生产得到普及,美国制造业效率提升300%,催生消费社会。
6Helpman & Traitenberg(1994)指出蒸汽机、电力、信息技术等通用目的技术,因其广泛渗透性、持续改进潜力 及互补创新效应,将成为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机制 上,通用目的技术具备普适性(Generality,可应用于多个产业,如电力赋能制造业、服务业)、动态改进性(Improvement,技术性能随时间持续提升,如摩尔定律下的芯片算力)、创新互补性(Innovation Spillovers,催生次级创新,如互联网衍生出电子商务、社交媒体),可以通过减低生产成本、重构生产组织方式以及形成技术生态系统影响经济增长。7Lipsey et al.(2005)进一步将通用技术分为产品、流程和组织三类,在人类有史以来的 24 种通用技术中,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对应的有18 世纪晚期到19 世纪早期出现的蒸汽机、工厂制以及19 世纪中期出现的铁路和铁蒸汽船;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对应的有19 世纪晚期到20 世纪中期出现的内燃机、电力、汽车、飞机和大规模生产;20 世纪70 年代之后出现的通用技术则包括互联网、计算机、生物技术和纳米材料,这些通用技术对应的是第三次工业革命。
8Akcigit & Kerr(2018)将垂直创新与水平创新相结合,提出了突破式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和渐进式创新(follow-up innovation)这一异质性创新概念。企业进行突破式创新旨在开辟新的产品线,而渐进式创新则专注于提升现有产品的质量。每一次突破式创新都会引发重大技术变革,并推动一系列后续的积累性渐进创新。
这一创新框架进一步揭示了通用目的技术扩散的微观机制。通用技术并非“即插即用”,其在经济中不同部门的广泛应用依赖于渐进式创新的不断优化。每一项渐进式创新都在推动通用技术与特定行业需求的深度融合。例如,生产装配线是电力革命在汽车制造领域的渐进式应用,而在线购物则是信息技术革命在商业服务业的具体落地。
这类渐进式创新不仅优化了企业生产工艺,还显著提升了生产率。然而,由于次级创新的推进需要时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经济增长的滞后性。此外,企业在进行渐进式创新时,需要从现有生产活动中抽调部分资源,这可能在短期内对GDP 增长率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重要概念“索洛悖论”。我们在前期报告《人工智能对经济的中长期影响:一个宏观框架》中曾做过介绍。1987 年索洛指出“计算机已经无处不在,但在生产率统计方面却看不到”,即新技术对于经济的影响,没有想象中那么显著。通用技术扩散假说可以为“索洛悖论”提供新的解释视角,它涉及“时滞效应”与单一通用技术的“涟漪效应”。9David(1990)以电力为例,论证了一项重大发明若要对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往往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扩散和应用周期。而从更宏观的技术变迁角度来看,10Freeman et al.(1982)指出,如果技术创新只是由许多不连续的基础性发明随机分布而来,并且不同技术的S 型扩散曲线各异,那么这些创新只会在经济体系中激起零散的“涟漪效应”,难以形成大规模的生产率波动;但若某些创新具有长期影响,并且彼此之间由于技术、产业、市场等因素而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那么就可能触发技术革命级别的深远变革。
我们在前期报告《人工智能对经济的中长期影响:一个宏观框架》中曾提到,按照现有GDP 核算体系,在人工智能未来的大规模应用中,现实的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增长率可能阶段性下降,因为人工智能必将导致一些商品与服务被替代掉,而新创造出的产品与服务,其增加值可能还无法核算,不能反映计入GDP 中。这一现象或将与与计算机时代的“索洛悖论”类似。为了解释生产率悖论,11Brynjolfsson(1993)指出,“投入产出的测度误差是悖论产生的根源”“由于IT 技术所带来的产出质量优化、产出类型增加、消费者服务提升等产出收益被传统核算方法所忽视,这造成了生产率的系统性低估”。
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例,虽然始于1971 年,但在1970-1990 年间,劳动生产率增长仍然受到索洛悖论的约束,信 息通讯技术(ICT)对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提升不足 20个百分点。然而,在1990-2020 年间,信息通讯技术的经济影响开始全面释放,其对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增长幅度是此前20 年的五倍以上。这一过程充分验证了通用技术扩散的“时滞效应”以及技术创新叠加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从上述框架我们可以理解一个重要的现象:为何在过去五轮技术革命周期,人类倾向于高估技术在“导入期”的影响,低估其在“展开期”的影响。其原因包括:一则“导入期”新技术打破既有部门分工和专业化过程的难度往往被低估;二则,研究者往往重视技术规律,忽视经济规律。新技术需要有一个逐步扩散的过程,只有当新技术体系内部形成有机关联并渗透至传统行业,催生新部门的快速增长,才能真正带来持久显著的经济影响,而这一过程往往是出现在技术“展开期”;三则,金融市场往往对于新技术的预期有一个“瞬间普及”的效应,甚至在部分时段伴随一定程度过度预期,但现实产业的演进有着自身的规律。
按照12佩蕾丝的理论,每一轮技术革命之后,引发长波周期的关键在于新技术的产生及其向整个经济体系的深度扩散。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演化的阶段,涉及基础设施建设、技能人才培养、社会认知转变以及制度环境的适配。只有当新的基础设施建立起来、拥有合格技能的电工和技师随处可见、消费者态度和法律环境对新技术更有力的时候,新的电气器材才能扩散开来。因此,不仅仅是技术的连续创新,配套基础设施的建立与制度的完善同样至关重要。
技术革命往往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和新兴产业的崛起,但旧部门的抵制力量不容忽视。19 世纪初,英国处于第一轮工业革命的高潮,纺织业逐渐从手工生产向机械化生产转变。随着动力织机的普及,传统手工工人被替代。
英国的纺织工人发起了“卢德运动”,摧毁纺织厂的机械设备,甚至威胁和袭击那些引起新技术的工厂主。1811-1813 年,卢德派在诺丁汉、兰开夏等地的大规模暴力行动导致英国政府派兵镇压,并最终颁布法律将破坏机器定为死罪。19 世纪中期,铁路的发展与建设对运河造成了威胁,运河投资者和运河公司意识到自身利益可能受损,纷纷采取措施阻挠铁路的扩张。他们通过政治游说,试图在立法层面限制铁路公司的融资和建设权利;同时,他们通过降低运费展开价格战,以吸引货运客户并延缓铁路的市场渗透。
就铁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13弗里曼等(1983)指出,铁路的意义远超运输本身。它不仅提高了煤炭和铁矿的流通效率,更为美国商业界提供了管理和运营大型组织的首个成功范例,例如高度准时的调度体系、远期服务规划、定期维修等现代管理理念。相较于运输成本的降低,生产组织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或许才是铁路对经济发展最深远的影响。
新技术不仅催生了全新的行业和部门,推动了新兴产业的发展,还深刻改造并升级了传统产业,通过不断重塑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赋予其新的生命力。以农业这一最古老的行业为例,在不同工业革命阶段,农业都经历了深度变革,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农业实现了机械化,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电气化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农业逐步迈向自动化,智能化生产逐渐成为趋势。
14Rousseau(2010)将通用技术所属时代的起始时间界定为该技术在家庭或制造业中采用率突破1%阈值的时点,同时将时代的终结节点定义为技术扩散曲线趋于平缓、进入稳定平台期的时点。按此标准,15程文(2021)将1970 年设为信息时代的起点,将2010 年设为人工智能时代的起点,进一步,程文(2021)在对比信息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通用技术扩散与生产率波动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通用技术在生产网络中扩散,影响劳动生产 率增长的动态模型。这一模型显示在人工智能的识别与导入阶 段,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并不会引起生产率的提高,这个时期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产业构成的复杂生产网络中扩散不同步,且无形资本所占比重过高;而进入生产协同阶段和成熟阶段以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对生产率的提高有显著促进作用。
具体地,以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时,通用技术的扩散速度如何随着技术扩散程度与经济增长为例,技术演进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发展呈现出清晰的阶段化规律。16信息技术的扩散过程历经三个典型阶段:第一阶段是1970-1984 年的技术萌芽期,15 年间信息技术采用率仅达8.2%,体现出新兴技术初期的缓慢渗透特征;随后进入第二阶段,产业融合加速期(1984-2003),分为核心产业内部整合(1984-1993)和外围产业扩展(1994-2003)两个阶段,信息技术的采用率分别进一步提升到22.8%与61.8%,扩散速度相比前一阶段分别提升2.8 倍和2.4倍;第三阶段则是2004 年之后的成熟阶段,在2010 年附近进入通用技术扩散平台期,信息技术已扩散到绝大部分行业,步入饱和期,扩散速度较第二阶段下降36.4%。在此过程中,劳动生产率也呈现与技术扩散深度绑定的周期性波动。在技术导入前期(1970-1980),劳动生产率增速处于下降趋势,从1970 年的2.70%下滑至1980 年的1.31%,而在随后的通用技术生产协同阶段(1981-2001),劳动生产率增速转为上升趋势,从1981的1.32%上升至2001 年的2.91%,而在最后的通用技术成熟阶段(2002-2010),劳动生产率增速再次处于下降趋势,从2002 年的2.91%回落至2010 年的1.70%,其中1974-1994 年长达20 年的劳动生产率低增长窗口恰与"索洛悖论"现象重叠。当前人工智能发展初期出现的生产率增速放缓,是通用技术扩散导入期的必经之路。
随人工智能技术扩散的进一步加强,转入生产协同期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也将转为上升趋势。
我们再来看技术革命对于就业的影响。对就业来说,技术进步对总量失业率的影响取决于“替代效应”(Displacement Effect)与“创造效应”(Creation Effect)的相对大小,它替代一些就业岗位,也创造一些新的就业岗位。过去两个多世纪的历史经验(17Autor,2015)表明,并无证据支持总量失业率随技术进步而长期增加,这就是技术革命的“总量就业中性”假说。事实看也是如此,从农业机械化到工业自动化,再到信息革命,每一次技术变革初期人们对高失业率的悲观预测最终都被事实所证伪。历史一再证明,尽管技术进步会带来短期就业的结构性调整,但从长期来看,它不仅提升了生产率,也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并推动了工资增长,而并非导致长期大规模失业和工资下降。从内涵边际维度来看,18Wei Jiang et al.(2025)的研究倾向于认为,由于人工智能和劳动力之间是互补而非替代关系,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能会导致更长的工作时长。
对于就业总量来说,我们前期报告《人工智能对经济的中长期影响:一个宏观框架》指出,人工智能与之前历次技术变革类似,将通过“替代效应”与“创造效应”两个渠道影响就业总量,“替代效应”是指人工智能技术在应用推广过程中,通过对劳动要素的替代,导致部分就业岗位消失,出现“机器换人”的格局。“创造效应”是指人工智能通过效率、技术提升,提高生产率,一方面通过生产规模的扩大增加劳动需求,另一方面还可创造新岗位、新工种,从而弥补了岗位的减少。
长期来看,人工智能的对就业总量的影响取决于“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的相对大小;短期来看,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或增加失业率短期上升的可能。这是因为个体层面的劳动者很难在新旧职业岗位间实现无缝转换,而系统层面的劳动力要素的跨领域流动配置必然伴随效率损失与市场摩擦阻力( 19 Acemoglu andRestrepo,2018)。从推进过程来看,技术进步的不断演进对就业的影响呈现出阶段性差异特征。在技术进步导入期,新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在主要领域得到应用,但核心产业规模有限,对相关产业的扩散影响不大或尚未形成,此阶段技术进步对就业的破坏效应较明显,甚至会引发就业的下降。在技术进步拓展期,核心产业规模迅速 扩大,对相关产业的扩散效应也逐步呈现,创造出大量就业岗 位,同时就业结构也会发生明显变化。
20《工业创新经济学》指出,18 世纪60 年代法国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是真正的生产,但接下来的半个世纪,法国农业就业占比从80%降至25%,实际工资反增25%且就业稳定;19 世纪20 年代李嘉图学派担忧机械替代将压缩就业,然而后续50 年英国实际工资增加一倍且失业率平稳;19 世纪60 年代马克思预言技术深化下,“劳动生产率越高,工业后备的失业大军越庞大”,但1900 年前后英国平均工资接近翻倍,而失业率未见大幅上升;20 世纪40 年代控制论学者维纳预言计算机将引发技术性失业危机,实则此后的40 年间美国时薪累计增长超100%,失业率仅微升1-2 个百分点。
尽管总量影响有限,但结构影响仍值得关注。劳动力市场工作极化(job polarization)是一值得着重关注的现象。它是指在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过程中,高技能和低技能职业的相对扩张,而中等技能职业的相对萎缩,从而形成就业份额或工资分布上的“U”型趋势。劳动力市场极化现象有多种维度的解释,最为主流的解释是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是21Hicks(1932)、22Acemoglu(2002)提出并发展而来,其核心思想是“当要素投入比保持不变,若技术进步引起资本-劳动边际产出比增大,则认为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反之则偏向劳动”。技术进步的偏向性特征会使要素的收入分配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一方面,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使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另一方面,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替代了常规任务密度较高的中等技能职业。
23Autor et al. (2003) 提出了“常规化假设”,将工作任务分为常规型任务、抽象性任务和手工型任务,常规型任务指信息技术资本替代性强的工作任务,如记账、重复性的生产任务等;抽象性任务包括解决问题、协调问题和管理等高技能任务;手工型任务则是如驾驶、安保等低技能服务型任务。24Autor & Dorn(2013)进一步发现,低技能职业和高技能职业的常规任务密度较低,而中等技能职业的常规任务密度较高。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下,计算机技术替代常规型任务,从而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
劳动力市场极化现象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技术变革中均有所体现。例如,在第二次技术革命时期,工厂制度逐步取代家庭手工业,导致大量中等技能工人被低技能的童工取代,而与此同时,对掌控机器的高技能工人的需求则显著上升。随着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传统手工艺人被淘汰,童工雇佣数量迅速增长,19 世纪30 年代,童工已占纺织业从业者的近一半,并在煤炭行业中占据三分之一的比重。类似的现象在随后的历次技术革命的后期也有所显现,尤其是在发达国家,许多从事程序化工作的白领工人面临失业风险,而与此同时,高技能岗位和低收入岗位的需求却在不断增长。25吕世斌和张世伟(2015)的研究表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同样存在“极化”现象。
再进一步深入,技术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催生“就业形态”的变化。从历史规律来看,前三次技术革命主要是带来了工业的发展,带来部分就业形态“从土地到工厂”的转变;第四和第五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带来部分就业形态“从工厂到办公室”的转变。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的内在性质来说,长期来看或将催生以创造力、人机协作和个性化服务为核心的“从办公室到智能工作生态”。当然,这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就业形态经历了两次结构性跃迁,当前正站在第三次跃迁的历史临界点。首先,蒸汽机与电力革命等开启了就业形态的第一次空间转移,机械化浪潮下,“从土地到工厂”的转变具有三个显著特征:
劳动时间的标准化(每日工时从季节性耕作转为固定小时制)、技能要求的专业化(例如,瓦特蒸汽机维修技师成为新兴职业)、生产组织的层级化(泰勒科学管理理论催生车间管理制度等);其次,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推动就业形态进入第二阶段的"白领化"转型,带来了从“从工厂车间到办公室格子间”的转变,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大规模发展,开启了后工业时代就业形态的深刻变革;最后,伴随当下智能时代的到来,生成式AI 与具身智能等正在催生第三次就业形态跃迁,但这场变革也面临三重矛盾:一则,技术扩散速度与人力资本升级的时滞、二则,效率提升与伦理风险的博弈、三则,生产力解放与就业替代的张力,“从办公室到智能工作生态”也不会一蹴而就,将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从金融市场和资产定价角度如何看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影响?(1)整体来看,技术要素在跨过“索洛悖论”之后,将带来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从历史规律看,每一轮技术革命将最终对经济增长形成强有力的助推,并在某个时段显性作用于企业盈利、居民收入,甚至利率。我们不可能既相信技术的微观影响,又忽视它对于总量经济的红利;(2)人工智能为主的新一代技术发展迅速,从经验规律来看,已经初步出现了要素成本下降这一带来通用技术扩散的必要条件了,理论上后续将逐步会出现支柱部门的扩大、引致部门的形成,所以对关键部门应用场景的影响是主要线索,具备一定体量的传统经济部门或者商业形态是“土壤”;(3)不过依然需要重视的是,在技术革命“导入期”阶段,对单一通用技术所带来的“涟漪效应”应有充分预期,对其向“展开期”过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应有理性的认识,避免高估单一技术在导入期的影响。从“导入期”到“展开期”,要突破的不仅是技术规律,还有经济规律;(4)每一轮技术革命对全球分工和专业化的格局均会产生影响,要从全球宏观的角度认识这一影响。中国经济的存量人口红利、工程师红利和延迟满足红利等三大要素优势将对应着其可以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实现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风险提示:全球关键通用技术的发展过程存在波折;全球关键通用技术发展过程中面临伦理、法律、基础设施、安全和市场等多方面的挑战;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海外贸易政策逆全球化风险;房地产市场的尾部风险。
*免责声明: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
*风险提示: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本站内容源自互联网,如有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请联系删除相关内容。 本站不提供任何金融服务,站内链接均来自开放网络,本站力求但不保证数据的完全准确,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均与本站无关,请自行识别判断,谨慎投资。